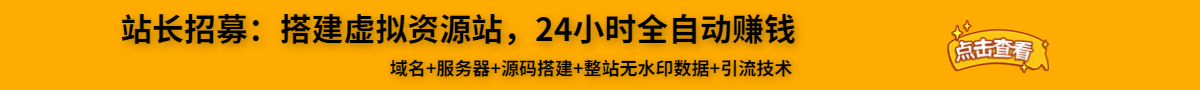限 时 特 惠: 本站每日持续更新海量各大内部创业教程,一年会员只需98元,全站资源免费下载 点击查看详情
站 长 微 信: muyang-0410

汪曾祺作品的主题,直接与他的人生观、世界观有关。他给人感觉很温馨,他“认为人类是有希望的,中国是会好起来的”,但他仍然是属于“自我的”作家。汪曾祺逝世以后,他的子女写了一本很好的书《老头儿汪曾祺》。我注意到一个细节:
爸爸写东西习惯一次成型,最多改过一遍。但也有例外。他的《寂寞和温暖》文末就注明:一九八〇年十二月十一日六稿。一篇小说写了六遍,在爸爸来说是绝无仅有的。这主要是家人审查的结果。
《寂寞和温暖》并不是爸爸主动要写的,而是家里人的提议。当时描写反右的事情的小说很多,像《牧马人》《天云山传奇》,影响都很大。妈妈对爸爸说:“你也当过右派,也应该把这段事情写写。”在家里,妈妈绝对是说话算话的一把手。爸爸想了想,于是便写起来。写成之后我们一看:怎么回事?和其他人写的右派的事都不太一样。没有大苦没有大悲,没有死去活来撕心裂肺的情节,让人一点也不感动。小说里沈沅当了右派,居然没受什么罪。虽然整她的人也有,关心她的人更多。特别是新来所长挺有人情味,又让她回乡探亲,又送她虎耳草观赏(这盆虎耳草显然是从爸爸老师沈从文先生的小说《边城》中搬过来的),还背诵《离骚》和龚自珍的诗勉励她。这样的领导,那个时代哪儿找去?纯粹是爸爸根据自己的理想标准生造出来的。不行,文章得改,向当时流行的题材看齐,苦一点,惨一点,要让人掉眼泪,嚎啕大哭更好。“老头儿”倒是没有公开反对,二话不说便重写起来。写完通不过,再重写一遍,一直写了六稿。最后一看,其实和第一稿没什么区别,还是温情脉脉,平淡无奇。大家都很疲惫,不想再“审”了,只好由他去了。
在这段很诙谐的文字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一个人的人生修养对创作的影响。人们在《寂寞和温暖》中,见不到作家把知识分子的痛楚昭示世人汪曾祺代表作,见不到反右是一场民族的大劫难。他的子女解释道:“爸爸仍然觉得,人们以前受的苦、受的罪已经不少,现在好不容易过得自在一点,实在没必要再把那些陈年老账翻腾出来,弄得大家心里憋屈难受。一个作家应该通过作品让人感觉生活是美好的,是有希望的,有许多东西弥足珍贵。因此,无论是写旧社会的社会生活,还是写解放后办的一些错事,爸爸都是虚化苦楚,渲染真情。‘美化’生活,就是他那个时期的‘创作主旨’。”
实际上,他写不来“苦楚”。他的人生品性和做文风格早已定型。面对苦楚,“随遇而安”,苦楚也变得美好起来。他能写出“让人掉眼泪,嚎啕大哭”的作品吗?不能。他自我把心理调节好了就可以了,他不会著文警示世人,更不会像巴金要建“文革”博物馆一样,提议建一个右派博物馆。根本上说,汪曾祺是唯美,他要表现美。
有个事情很有趣,值得一提。汪曾祺人称美食家,林斤澜把自己叫做“食美家”。但两位的朋友邓友梅在《再说汪曾祺》中却写道:“汪曾祺近年来被人们称为‘美食家’,我很高兴,也为斤澜抱不平。五十年代斤澜的烹调不在曾祺之下,他做的温州菜‘敲鱼’在北京文艺界独此一家。他家吃菜品种也多样。曾祺桌上经常只有一荤一素。喝酒再外加一盆花生米。”另一位军旅作家陶大钊在《海鲜》中写道:“林先生不仅会吃海鲜,还会烧一手好鱼,一条几斤重的大鱼在他手里,能做出一席鱼宴来。有人曾经把汪曾祺和林斤澜烧的鱼作过比较,结论是林斤澜技高一筹。”
实际上,林斤澜写吃不如汪曾祺,写吃文眼不在吃,汪曾祺写吃就写吃,写得比烧得还要好。他的散文实在漂亮,叫人心动。如写《扦瓜皮》:
黄瓜(不太老即可)切成寸段,用水果刀从外至内旋成薄条,如带,成卷。剩下带籽的瓜心不用,酱油、糖、花椒、大料、桂皮、胡椒(破粒)、干红辣椒(整个)、味精、料酒(不可缺)调匀。将扦好的瓜皮投入料汁,不时以筷子翻动,使瓜皮沾透料汁,腌约一小时,取出瓜皮装盆。先装中心,然后以瓜皮面朝外,层层码好,如一小馒头,仍以所余料汁自馒头顶淋下。扦瓜皮极脆,嚼之有声,诸味均透,仍有瓜香。此法得之海拉尔一曾治过国宴的厨师。一盆瓜皮,所费不过四五角钱耳。
请问海拉尔治过国宴的厨师,能写出这样的文字吗?
汪曾祺看世界用两个字——凝视。这个词主观也直观,感情也感性,是静态的。他看世界的眼睛非常明净,世界一片蔚蓝。他自己说“我没有什么深奥独特的思想”。他才华横溢,有着超人的形象记忆力。描写很精细,很精到,很精妙。他追求的是美,达到的是和谐。他确实是达到了,这是他的优长。这种优长很容易在散文上得到熨帖的发挥。我一直觉得,汪曾祺散文的成就超过小说,而他的小说也几近散文,散文上多了一二情节,或者说,汪氏小说就是散文化的小说。
比如说《受戒》开篇:
明海出家已经四年了。
他是十三岁来的。
这个地方的名字有点怪。叫庵赵庄。赵,是因为庄上大都姓赵。叫做庄,可是人家住的很分散,这里两三家,那里两三家。一出门,远远可以看到,走起来得走一会儿,因为没有大路,都是弯弯曲曲的田埂。庵,是因为有一个庵。庵叫菩提庵,可是大家叫讹了,叫成荸荠庵,连庵里的和尚也这么叫。“宝刹何处?”——“荸荠庵”。庵本来是住尼姑的,“和尚庙”“尼姑庵”嘛。可是荸荠庵住的是和尚。也许因为荸荠庵不大,大者为庙,小者为庵。
一二两节看得出是在写小说,第三节完完全全是散文的笔调。《受戒》不短,可是表现故事情节的大约只有三分之一。《大淖记事》也是如此,全文约一万四千字,开篇闲聊的文字便有三千字,闲聊什么呢?大淖风俗。第二节结尾主人公十一子出现了,一出现就立刻闪逝。第三节全是风俗画,没有故事。女主人公巧云是在第四节出现的,她的生平,她的琐事,汪曾祺全是聊天式地描写,这一节的结尾,男女接触,好像故事要开始了,可是篇幅八千字拿走了。第五节,情节又断,写水上保安队和号兵的事,又是另外一幅风俗画。这一节即将结束,“巧云找到十一子,说:‘晚上你到大淖东边来,我有话对你说。’”才在沙洲上野合,算是故事发展了。但,就那么几行字,“月亮真好啊!”结束了。第六节,最后一节,汪曾祺不讲故事是不行了,要散架了,便全力讲,字数两千多字。同样,讲故事差不多五千来字,也就是全文的三分之一。

汪曾祺代表作——《受戒》《人间草木》书影
汪曾祺不会讲故事吗?不,他是才华盖世的艺术家。可是,没有一位作家没有局限。看得出来,汪曾祺形象思维强,而逻辑思维弱。而且没有一位作家是不受自己的人生经历限制的,作家只能讲自己熟悉的故事,自己喜欢讲的故事,能够表达自己观念的故事。艺术多元,各用各的嗓子唱歌。不用说,《受戒》就是杰作,玲珑剔透、美轮美奂、无可挑剔、炉火纯青,是流芳百世的杰作。当然,我所谓讲故事指的是小说笔调,汪曾祺的小说是用散文笔调写的。他自己就说:“我的一些小说不大像小说,或者根本就不是小说。”汪曾祺又说:“有人说,小说跟散文很难区别,是的。”汪曾祺的散文又那么多,那么好,所以,整体上汪曾祺还是以散文见长。或者索性这样说:汪曾祺是当代无与伦比的散文泰斗。
汪曾祺的老同事、剧作家阎肃这样评价汪曾祺:“他不擅长结构剧情,长处在于炼字炼句。写词方面很精彩,能写许多佳句,就是在夭折的剧本里也有佳句。”《杜鹃山》导演之一张滨江说:“《杜鹃山》的押韵念白,汪曾祺写起来得心应手。他的火花太多,文字滋味浓,很鲜美。”
汪曾祺在《林斤澜的矮凳桥》里说:“斤澜是很讲究结构的。我曾在一篇文章里写过:小说结构的特点是‘随便’。斤澜很不以为然。后来我在前面加了一个状语:苦心经营的随便,他算是拟予同意了。”这个意思,他在《自报家门》中也写到过。我想,“苦心经营”一是得意了自己,二是安慰了林斤澜,其实他的心中只有“随便”二字。因为,汪曾祺的小说就用不上“苦心经营”,或者干脆说,汪曾祺的小说就用不上“结构”。
我说这话并非危言耸听,汪曾祺的小说也太像散文了,或曰:“就是散文也需结构啊。”是的,而一旦有话要写,对于才气过人的汪曾祺来说汪曾祺代表作,是啥子事嘛,略加“组织”(乃师把结构叫做组织)就是了。他自己说:“我永远是一个小品作家。我的一切,都是小品。”而且,他一再提倡“短”。“短,是现代小说的特征之一”,“短,才有风格。现代小说的风格,几乎就等于短”,“短,是出于对读者的尊重”,“短,也是为了自己”——像是画一个册页,一个小条幅,汪曾祺用不着冥思苦想、“苦心经营”,稍为踌躇,提笔可画。因此,他能做到如苏轼所云“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
因此,“随便”只能适用于汪曾祺本人,及其类似的作家。曹雪芹是不成的,托尔斯泰是不成的,福克纳和马尔克斯也是不成的。汪曾祺是反对写长篇的,认为长篇虚假,一个人没那么多东西可写。实际是他个人的事。他也打算写个长篇——《汉武帝》。我想,延寿十年,他可能也写不出来。林斤澜作文推崇汪曾祺的《陈小手》,我以为《陈小手》的确不错,接生的男人骑白马在田野里飞奔,英姿十足,接生后被团长一枪打死。但,这一篇好像不是汪曾祺的小说,“白马”编造痕迹明显,最后这一枪更加刺目。他讲故事讲不好:如他的风格可不可以不死呢;这一枪也是从法国作家梅里美那里搬来的,他可能早已忘了。
林斤澜与鲁迅有许多相同的地方,比如追求深刻,讲究结构。林斤澜的结构形态比鲁迅还要多样,甚至走得更远。对于小说的最高境界,作家曹文轩有“精致论”,作家李敬泽有“极致论”。我认为林斤澜追求的是极致,汪曾祺追求的是精致。

汪曾祺(右)与好友林斤澜 作者供图
林斤澜对汪曾祺的意见,一般都能听进。有一回,汪曾祺对林斤澜说:“你的小说,紧绷!”林斤澜就怀疑自己了。这实际上是汪曾祺结构观的问题。他自己的文章太随散了,太舒缓了。邓友梅在《再说汪曾祺》中写道:“1957年反右之前,斤澜在《北京日报》发了篇小文章,谈文艺观点,一千来字。字斟句酌,行文严谨,不少人看了叫好。曾祺却对我说:‘你见到斤澜跟他说一声,讲究语言是他的长处,但过分考究难免有纤巧之虞。这么篇小文章,何苦啊……’我跟斤澜转达了。斤澜听了满服气,不断笑着点头自语:‘纤巧,哈哈哈,纤巧,哈哈哈哈……’”
晚年,汪曾祺对林斤澜说:“你的语言,佻!”林斤澜也是哈哈哈哈笑。佻就是轻薄。这话就说重了。那为什么林斤澜还哈哈哈笑呢?我以为,除了雅量之外,他是真正佩服汪曾祺的语言的。在北京一个会上,林斤澜一反常态,公开说:“论语言,在男作家中,汪曾祺第一;女作家中,宗璞第一。”据说女作家中有人不同意,男作家人人服气。
林斤澜还有一句话,我听过不止一二回:“别的不讲,论语言,五十年来汪曾祺应当说是最好。”
汪曾祺写小说《徙》的开头,原来是:“世界上曾经有过很多歌,都已经消失了。”他总觉得不满意,难以下写。后来他出去转,回来就改成一句:“很多歌消失了。”写下去就比较顺畅了。这件事也叫人想起“环滁皆山也”。
汪曾祺是把白话文写到顶点的一位作家,是把古典文学的气韵同口语结合得最好的一位作家。他脱离了朱自清的贵族气和文绉绉,也没有老舍的文艺腔和翻译体,比赵树理更有文人的底蕴,更经得住咀嚼。
文章出处:《北京文史》2016年第3期《情到深处——回忆作家汪曾祺》
限 时 特 惠: 本站每日持续更新海量各大内部创业教程,一年会员只需98元,全站资源免费下载 点击查看详情
站 长 微 信: muyang-04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