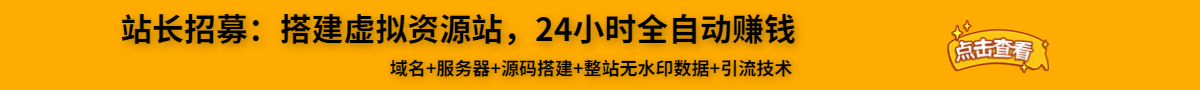我是1974年7月高中毕业,我一直以为这是“文革”期间最特殊的一届高中毕业生,因为这是严格考录的一届高中生,而且,参加考试的初中生囊括了四届小学毕业生。我们读了两年半,初中也读两年半,初、高中合计读了5年。很多同学都说我说错了,没有两年半的学制,都是两年。学制是学制,我们正巧两次都处在改学制的节点,所以都读了两年半。我在这里记述如下,请本届的老师和老同学们帮我一起回忆、回忆。
我是1966年秋季入读五年级的。我们大队的小学只有四年级(初小),临边大队办到六年级(高小,也叫完小)。我和一位同学去报名的路上,看到家家户户的墙上都涂一块方形的“语录牌”,从语录牌就可以判断一个家庭的成分,比如,白底黑字的准是“四类分子”家庭,内容通常是:“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如果是红底黄字、写着“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的,肯定是贫农成分。开学后不久,中学校就“停课闹革命”了,所以,66级的初中生就没上成,有的回家了,有的参加红卫兵大串联了。我邻居的孩子是农业高中,他就去串联了,春节前给家里来信说,一路上坐火车、吃饭住宿都不要钱,他们正在去韶山,然后去北京见毛主席。全村的人、特别是年轻人都羡慕死了。我们没有停课,每天两节课,然后是劳动——割草或扛石头。没有语文和数学,改为语录和珠算。语录是32开本,0.2元,很快就流行64开塑料皮的(红宝书),0.45元,还有更小的袖珍本。我们大部分时间除了劳动,就是开批判会,主要是批判校长,偶尔也批班主任或某个老师。教我们珠算的老师,特别严厉,从无笑脸,哪个学生在课堂上说话,或者做小动作,他张口就骂,甚至打。说来奇怪,只有他没被批判,也没人贴他的大字报。
1967年读完六年级,我们也停课了,直到1969年秋“复课闹革命”,这个大队第一次办初中班,我们才继续上学。所以,这是66、67、68、69四届小学毕业生同时升入初中,当时叫“戴帽班”。由于严重缺乏师资,我们只开了语文和数学,物理、化学、历史和外语都没人教,为了照顾这个现实,高中升学考试只考数学,另外写一篇作文,题目是《记一次批判会》,实际上等于只考了一门数学。
我们是1971年寒假毕业,而且学制改为二年,之前都是暑假毕业,理由是,暑假是农忙季节,老师们必须参加劳动,寒假是农闲季节,老师们有时间处理业务。就在这年秋季,公社经常组织传达“绝密文件”,搞得人心惶惶。年底便传说:初中升高中不再“推荐和选拔相结合”了,一律按考分录取。理由是,初中生已经没有“四类分子”子女,都是贫下中农的孩子,怎么推荐?我们考试的时间是1972年春节后,具体日期记不清了,只记得当时都在议论尼克松访华。那是我这一生经历的最严肃的考场,一位主考,两位监考。
经历这次考试升学,同学们都特别重视学业,尽管很快就发生了“黄S事件”、“交白卷事件”、“马振扶公社事件”,大批“南方教育经验”等干扰,但大家学习的自觉性并没有减弱。
1973年底我们应该毕业,可巧,毕业时间又从寒假改回暑假,我们又多读了半年。但是,教学大纲已经进行完了,这半年基本上由老师们自主安排。我一直认为,这半年相对自由的(没有高考任务)教和学,使我们收益最大。那是最好的教育方式,我们今天谈教育改革,应该从这一届高中教学中汲取智慧。
所以,虽然当时的中学学制是二年,我们却读了两年半高中。不知是否准确?恳请网友们指正。
另外还有几件琐事顺便记下。
我们初中以前的作文主要是两方面的题材,一个是心得体会,一个是批判文章。我觉得,这对我们的人格形成影响最坏最深小学毕业时间,它塑造了我们的两面人格——撒谎。因为,这两类作文多数都是在编造谎言。一方面,不可能有那么多“好事”被我们这些孩子们遇上,即便偶尔遇到一次,也未必就是遵照老人家的教导去做的。另一方面,批判的对象多数都是虚拟的,即便实有其人,他的“反动言论”或“反动行为”也是虚构的,因为,一个少不更事的孩子,怎么可能经常接触这些“反动的”东西呢?即便偶尔接触过,又怎么可能作出政治上的判别呢?
还有一件事可作对照,我们临村的一位公社级的“典型”,40多岁的妇女,到处作报告,远近闻名。她被树为“典型”的原因是,有一次她路见一堆牛粪,用头巾包着交给了生产队。她经常背着粪框到处溜达,遇到劳动的人群,便手舞足蹈地唱起来。我亲眼见过,她可以唱一段诵一段把《为人民服务》背下来,确实神奇。但这能说明什么呢?
我们这里大约在1970年前后普及了有线广播。我认为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事业!它不仅打破了农村千百年来的闭塞状况,为动员和组织农民提供了空前有效的手段,而且还成为改善农民日常文化生活的主要平台。当时每天晚上广播里都有文艺节目,除了地方戏,主要就是教唱样板戏,许多青年就是跟着广播学会了样板戏的唱段和普通话的。这个举措值得大书特书。
关于“红卫兵”。运动开始时只有成人、或者中学以上的学生才能加入,我们这些小学生都不够格,我见过父亲拿回家的红袖章。后来有“红小兵”,我们又进入中学了,年龄大了。在初、高中阶段,也没有举行过加入红卫兵的仪式,所以,我们都是“白皮”。与各种“战斗队”走马灯似的登场的同时,各大队又争先恐后、不讲条件地成立宣传队。我们大队就拼凑了个宣传队,排练的剧名叫《夺印》,从未演出过,可那些队员们照样记工分,社员们议论纷纷。
还有一件事令我终生难忘:高中第一年冬季,全国热映一部电影《卖花姑娘》,我们这里只在县城放映。星期六下午,同学们决定去县城看这部电影。我们距离县城30多里路,中午我就断了干粮,只剩下半张稻糠煎饼。赶到县城,买到9:20的票,二毛钱一张。看完电影已是半夜12点,我们往回赶的时候还没觉得饿,走到一半路程,大家都饿了,又累又冷,大家都在算计哪里能找到吃的,哪怕野菜也行。天太黑,又是冬天,根本不可能找到吃的。有人提议歇一歇,但多数人认为不能歇,因为那就再也走不动了,会冻死的。于是大家边走边讨论,回学校还是回家?因为学校食堂附近窖藏的萝卜可以充饥。最后还是决定回家。我和另一位同学路程最远,当我走到家门口的时候,还是想坐下来歇歇脚,那位同学坚决不同意,他要看着我推门进家。我真得感谢他,他还要走一里地才能到家,却为我担心。几乎是空腹步行70里,现在想想真不知道怎么挺过来的?后来我问那位同学,为什么他比我能撑?他说,他出发前吃了两张煎饼,掺的不是稻糠小学毕业时间,是山芋干,而我只吃了半张掺稻糠的煎饼。
(图片来自微信群,不知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