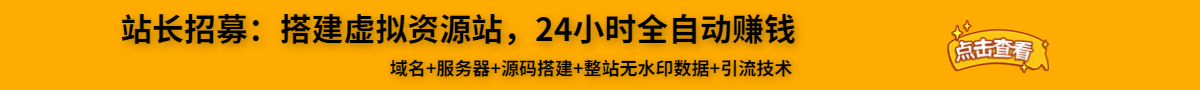解读俄罗斯战斗民族的军事传统、战略思维和民族性格。
探索一流军队建设之路!
《军中三剑客》将陆续发布《我在伏龙芝学军事》一书中的精彩章节,欢迎关注并留言讨论!
第八节:“外语高手”有时会气馁
出国留学是一次难得的学习和生活经历,国家实行“三保障”,自然令人羡慕。 吃洋面包的滋味,或许只有我们这些吃过的人才会有真正的苦乐参半的感觉。
无论你去哪个国家留学,无论你是公费生还是自费生,你首先会遇到和解决的问题就是“语言障碍”。 我们出国留学的军人也不例外。 根据中俄两国签署的相关协议,我校三年制中级班学生全程俄语授课,无需翻译。 这是自中国改革开放至2013年以来,解放军派出时间最长的一批军事学员。在此期间,就读于俄联邦总参军事学院的高级班学员,一般要花一到半年的时间。有一年的口译员。 中级班学生毕业后出国留学时间改为2年制或1年制。 随着俄军“重塑军队新面貌”改革和军事教育体制调整的推进,2013年起,中国留俄军官中级班恢复三年制学制,一年的预科课程和两年的专业学习。
赴伏龙芝军校留学的12名校级军官分别来自司令部机关、军区部队、军校和科研单位。 从年龄上看,最小的30岁,最大的38岁; 学历方面,均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其中军事硕士4人; 军衔方面,上校2人,中校5人,少校5人; 俄语水平上,有两个是本科毕业的,一个是读中学的,另外几个同志连俄文字母都不会。 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出国旅行都是从学习俄语的 33 个字母开始的。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
1996年4月至8月,从解放军各大单位选拔出的数十名预备役军官集中在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进行俄语集中训练。 总部领导和学院领导高度重视。 俄语教研室主任张瑞珍亲自参与,混合搭配了老、中、青年教师,还为我们开设了很多课程,如对外军事、国际关系、外交礼仪、计算机等。
巧合的是,这所学院是我的母校,南京是我学习生活了4年的第二故乡。 10年前,我离不开与我日夜相伴数年的大学同学。 我满怀报国强军的热情,被分配到青岛海军工作。 一个亲切的,兴奋的回家。
首批外国军人俄罗斯强化班结业典礼
回到故地,触景生情,教学楼、宿舍楼、食堂、足球场、礼堂、梧桐树时常让我想起那些年的故事。 但在我的记忆中,最难忘的还是学习俄语的艰辛。 中学时,我为了“反修”和“反霸权”学了俄语。 我用的是辽宁省的课本,只有几十页厚。 没有忘记。 1982年全国高考,他在百分制的俄语科目中取得了94分的高分。 别说什么基本功,全靠死记硬背。 进入军校后,他接受了听、说、读、写、译“五种能力”全方位的专业训练。 他上午看书、上课、晚上自习,穿梭于教室、宿舍、食堂“三点”之间。 为了学好俄语,我确实付出了很多努力。 其中,我在学生时代患过12次咽炎,3次中暑。 至今记忆犹新,一提到“南京”就有些后怕。 夏天“火炉”的味道让我这个北方人受不了。 医生说,咽炎是学外语的“职业病”。 老师说,就算你得了几次咽炎,也学不好外语。 看来得了咽炎跟学外语有一定的关系。
学习外语是无聊的。 成天和字母的组合变化打交道,需要良好的记忆力、机智和文学水平,还要在“童技”上下功夫。 知道自己没有那种天赋,外语只是工具和拐杖,单靠外语是路窄,发展有限。 1989年参加工作3年后,以总分第一名的成绩考入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科学专业。 硕士学历,专攻军事战略。 毕业后留在军事科学院军事战略研究室,从事军事战略、国家安全战略、邓小平战略思想等方面的专业研究。 俄语在工作中基本用不到,离我越来越远,越来越陌生。
没想到,大学毕业10年后,我又重操旧业。 或许我这辈子就与俄语和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结下了不解之缘,机会难得。 事实是一样的。 1988年和1989年两次参加全国研究生考试,备考期间外文基本不读。 我把大部分精力和时间都花在复习军事战略、军事历史、作战规章等不熟悉的专业知识上。 外语考试成绩还在80分以上。 2004年,解放军总部决定从留学归国的军校学生中选拔军事外交后备干部。 我有幸成为9名候选人之一,2006年赴中亚在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馆任职,并再次在俄罗斯从事军事外交工作近3年。 上任前,他回到南京母校进行了两个月的商业学习。
1996年南京留学军事外语强化班,我和俄语班的几位同学被指定为“小老师”。 虽然我有一个恢复和提高的过程,但主要任务是帮助那些以前没有学过俄语的学生。 ,教给他们一些学习方法,记录课文,解释词汇和语法等等,大家都叫我们“外语大师”。 的确,对于我们这些学过俄语并接受过专业培训的人来说,从零开始精通俄语太简单了。 5个月的时光令人难忘,我们结下了深厚的战友情谊。 大家都明白,虽然我们来自五湖四海,但我们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留学目标走到一起的。 每个人的人生起点和终点都是一样的,只是过程经历不同,所以人生的过程才是最重要的,相遇相识是难得的缘分!
“俄语真的很难学,尤其是语法最难学,变幻莫测。” 我们中的绝大部分都是英语出身,很多人都达到了国六水平。 这样的情绪。 俄语最大的优点之一就是读和写基本一致,有点像汉语拼音。 但是,俄语不同于汉语等象形文字。 它是一种基于形式的语言。 词义本身与词形没有直接的意义联系,需要通过形式分析来理解语义。 在构词方面,俄语多为派生词,借助一个词缀生成多个词,习惯用概括词来表达具体事物; 在构词造句方面,名词、形容词、代词等有“性、数、格”变化,动词有“时、体、态、格”等变化,突出主语的中心地位和谓词; 在连句的构成中,写作中多采用带定语的引申句,标题直指开头,先有关键词和主句,然后依次显露。 主句或主句中的词汇; 表达思想时,围绕主语和主句,由主到副,由小到大,由点到线,按线性顺序叠加,逻辑性强,把握度强,线性精确。 可以说,只要两个词放在一起,就会出现词汇问题。 说话或写字时,一定要想好词尾,严格遵守语法规则。 难怪大家都说俄语一个名词其实是12个名词,一个动词有20个。多种动词呈现方式。 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俄语复杂的结构和特殊的思维方式俄文字母,也反映了我们留学生活的艰辛,需要面对全新的文化氛围、民族性格和思维方式。 早年就读于伏龙芝军官学校的刘伯承元帅曾这样描述自己学习俄语的感受:“过了一年多,我开始学习外语,还没开始,朋友们就很担心。见证开始苏联成立的时候,我挨饿了。真心的,今天我买得起牛奶和面包。每次想起四川人满桌的菜,“豆腐”还是买不到。我更有动力了学条文,精兵报国,然而只是一门外语,这志向如何实现? ;视难为敌,昼夜攻克,数月能读俄书。 前辈、高级将领都可以做到这一点,我们新一代的军官没有理由不会或学不好俄语。 他们只能迎难而上,加班加点,废寝忘食。
“外语是人生斗争的武器”,这是马克思的一句名言。 但真正领悟其深意,恐怕要到留学之后了。 可能是因为已经过了学习外语的最佳年龄,也可能是因为俄语太难学了,一般人都学得很吃力。 有人把学习俄语的过程形容为“掉一根头发,记住一个单词”。 甚至在出国之前,很多同志还是发不出俄文字母“P”的颤音。 不过,当听说革命导师列宁和一些俄国人都不能把这个音发得非常纯正准确时,大家自然而然地得到了很大的安慰。 据说俄语“Россия”在汉语中译为“俄罗斯”而不是“俄罗斯”和“罗西亚”,这与俄语辅音“P”的颤音难发有关。 初学者和非俄罗斯人经常在“P”音之前添加“O”音。 曾经统治俄罗斯200多年的蒙古人习惯把“Россия”这个词读作“OROS”或“OROCCIA”。 中国晚清出版的《大清统史》,用“俄”代替“俄”、“罗刹”等名称。
语言是人们进行交流的媒介和前提。 它来源于现实生活,学好一门外语自然离不开一定的语言环境。 在我的记忆中,出国前只和俄罗斯人有过两次接触。 印象最深的是我在军事科学院读研究生的时候,1991年秋天参观北京国际航空展览会,与参展的俄罗斯工作人员进行了简短的交谈。 工作人员夸我俄语说得好,还赠送了一套俄罗斯航空装备明信片,但我自知这只是一种友好的姿态。 学了几年俄语,由于缺乏实践的机会,我渐渐生疏了,基本变成了“哑巴”和“聋子”,几乎把掌握的基本功还给了老师。 出国留学让我有机会重操旧业,在实践中恢复和提高。
我们在伏龙芝军校留学的第一年是预科,主要任务是学习俄语和熟悉军事术语。 只是所有的老师都变成了俄罗斯人,生活环境也变了。 正是这种变化使一切变得如此直截了当和一知半解。 如果不是在国内打下了基础,我在留学初期肯定和大家一样开明。 但话说回来,也正是这种变化,使我们能够学习到地道、规范的俄语,养成用俄语思考和做事的习惯,进而为准确理解和掌握军事专业知识和作战指挥能力创造了条件。
在没有翻译的情况下在军队留学是困难和痛苦的。 我和另一位毕业于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的“外语精通”学生盛跃中在伏龙芝军校留学期间,特别是预科期间,自愿为大家承担了一些“翻译”和“差事”。 其实我只是比其他同志多学了几年俄语,有了一定的词汇和语法知识。 在国外的时候,总觉得自己没有底气,也有气馁的时候。 我们的军官留学虽然都是有思想有理性的大人,但是论语言学习的效果,真的就像幼儿园的孩子。
刚到俄罗斯的头几周,我们都有刘姥姥进大观园的笨拙感觉。 我们基本上处于“半聋半哑”的状态。 和俄罗斯人交流很困难,我们甚至害怕俄罗斯人说话。 我既不能理解别人在说什么,也不能清楚地表达自己。 坐地铁听不到站名,过站是家常便饭; 当我去商店买东西时,我只是用手指要求“这个”和“那个”。 买肉的时候,分不清牛羊肉。 几只绵羊或母牛在咩咩叫; 想放松一下,但看了电影电视也搞不清楚别人在说什么主要内容。 大概的意思我能听懂,但不能多说。 此外,生活和学习是全方位的。
预备学期后半段,我们开始转入学习军事术语和战术常识,难度不是很大。 要说留学三年最艰难的时候,就是大二专业学习的前半年。 我们常常满怀信心地走进教室,却失望地走出教室。 这是因为我们的“讲授课”(лекция)就像听圣经一样,课后我们没有背几行。 这种课充满了讲座和报告。 其实就是老师们介绍军事学术前沿、军事实践需求和发展趋势的讲座报告。 老师布置的阅读和写作作业别说对我们来说有多难,别说一晚上也看不了几页,就算读了也不会给我们留下任何印象。 我借了很多书,有些书一页都没读就还给了图书馆。 学习完全是一种被动的应对方式。 学习很辛苦,但效果却不大。
我军选拔干部有的是营长、团参谋长,有的是专业技能过硬的机关主任、参谋,有的具有副教授、讲师、助理研究员等中高级职称。 是能独善其身的脊梁。 真没想到,在异国他乡,我被33个字母的组合弄得一头雾水,本来的一切优势都被俄语抹杀得一干二净。
因为进不去状态,我和大家一样很着急,处处觉得别扭,也对俄罗斯人和俄罗斯社会形成了极端的看法。 很多战友说,一直以来做任何事都信心满满,没想到被外语难倒了,会被判死刑。 甚至与俄罗斯人就一些问题争论不休,也很难打骂。 “说俄语更难,说汉语容易”成了我们经常自我安慰的一句口头禅。
经过一年的预科和半年的专业学习,我们的外语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专业词汇量有了很大的增长,基本适应了教学环境。 我心里有点底气了。 尤其是在各专业教研室老师的“连连轰炸”下,我们可谓是历尽坎坷,直到留学二年级下半年才顺利通过语言障碍。 倡议。 专业课、旅游、购物、跑腿基本可以自如,养成了一些俄式思维习惯,比以前踏实多了。
然而,留学毕竟远离祖国和亲人,在另一个与本国在语言、文化、习俗等方面有很大差异的国家,“语言障碍”问题自始至终都存在. 尽管我们努力工作,但不理解、误解、写错或不说话的情况并不少见。
记得有一次去莫斯科电器集市买录像机。 由于语言不通,经验不足,我买的机器是单机,只能播放不能录音,对学习和储存资料帮助不大。 只好回去改了。 我选了一台“东芝”牌录像机。 卖家说加价,结果我听错了,多付了他50多块钱。 还好佐治亚州的卖家好心把多出来的钱还给我了。 我不懂英文和法文,但俄文的数字听起来很费力,需要理解和转换,因为俄文没有“万”、“十万”、“千万”等计量单位的词,还要靠一万、十万、几万。 一百万字从何而来,再加上1998年金融危机前的俄罗斯卢布一文不值,10万、5万、1万面额的纸币经常被使用,时不时被天文数字困扰。 问人一两次还好,问多了就觉得尴尬。
在学习专业课方面,幸运的是,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师生之间默契度很高。 部分学生所学的作战战术和技术装备知识储备等专业优势逐渐显现俄文字母,让留学困难的局面变得轻松起来。 大大改善。 但在国外生活和学习是多方面的,所以我总觉得力不从心,没有融入别人的社会,没有真正了解俄罗斯人的内心世界。
(待续)
关于作者
郝志辉,祖籍内蒙古赤峰,出生于辽宁大连。 军事科学院战争研究所研究员,现居北京海淀。 1996年9月至1999年6月在俄罗斯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2006年8月至2008年12月在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馆工作。 主要研究国家安全战略、军事战略、世界智库和俄罗斯军队等问题。
《我在伏龙芝学军事》由现代出版社出版,本文转自中国军事网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