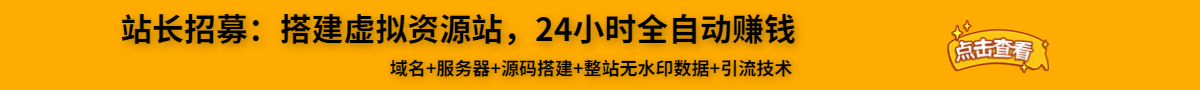这是奴隶社会的第2434篇文章
题图:2016年科蚪空间孩子们的“艺术照”。
作者:欧阳艳琴,曾经的留守儿童,曾任财新传媒调查记者,2015年创办流动儿童教育公益机构“科蚪”,2018年创办“实务学堂”,2018届银杏伙伴。
到今年六月,我从媒体离开,开始教育公益创业,正好六年。
六年不短,但回想起来,似乎也是弹指之间。
常有朋友问,创业、做教育,和做记者,有什么相同和不同吗?这六年,后悔了吗?
无论做记者,还是创业、做教育、做公益,我一直信奉一个原则,且把它当作我这一生最重要的原则,那就是 — 诚实。诚实意味着,做该做的,呈现的确有的,对没有得到的信息,或没有做到的事情,不要自圆其说。
我们这几年里创办的实务学堂,“校训”的第一条,就是“诚实”。
以下,是我对这六年创业的经历和感受,一个诚实的梳理。
结束和开始
我还记得六年前的细节:
在大明和舒立的办公室里,我突然有些想哭。在那之前,我写了一篇文章,公开告诉大家,我要离开媒体,去开始教育公益创业啦。
我热爱我的调查记者工作,但当下似乎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2015 年,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似乎全世界的教育都在创新,都在面向未来做变革,但是乡村、城市边缘地带的打工者社区死水一潭。我来自乡村,来自打工者社区,曾经是一个留守儿童,父亲至今也在东莞打工。我痛苦于这种割裂与差距,并且同时对教育兴致勃勃,觉得自己可以做出一件有意思的事。
最初的想法是做一个社区儿童空间,我觉得公共儿童空间应该是一个社区的基础设施。我希望让打工家庭的孩子课后有个安全、好玩的地方去,并且希望尝试一些创新教育。我还期待创新运营方式,不用依靠捐赠,做到自负盈亏。
这就是后来的“科蚪社区儿童空间”,诞生在我父母打工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工厂区。
▲2015 年 6 月,刚刚到东莞,租下场地,准备装修。
但眼下,我要办理离职,离开我曾经视为理想的工作岗位。
大明对我说:你要知道,现在,你不只是“试试”,而是在做一个职业道路的选择。因为,你也不是没在公益行业里试过。
那时候我还没有明白这句话。我还以为自己一年或者两年以后,就会回到媒体,重操旧业。大明懂一个人的职业发展道路是什么样的。
我还记得,6 月 9 号,踏上广州的土地时,尽管我已经许多次来到这里,但那一次,心情还是很不同。下了动车,我就已经想回北京去了。我还把箱子落在车上了,想起来时,已经走到了地下通道,幸亏车子还没开走。那时广州的马路上,还有掉落的小芒果,气温和现在,应该差不太多。
接下来的一个月,装修、参加培训、招志愿者、招学生、准备夏令营,直到 7 月 6 号,“科蚪空间”开业,每天都非常忙。
▲2015年7月6日,科蚪儿童空间在东莞厚街的工厂区开业。
但忙碌的日子里,占据我内心的,其实不是充实感,是不真实感,甚至有些绝望,至少是自我怀疑、孤独和不适应。因为我确实离开了我既有的轨道,和熟悉的生活工作圈子 — 回到了我父母打工生活的地方,一个并不是我熟悉的地方。没人知道我的情绪。那时开始,我要把自己训练成一个坚强的创业者。
一晃,六年就过去了。如果回到六年前,我还会做出同样的选择吗?我不知道。
去东莞
做“科蚪空间”的时间不长,只有一年半。我们尝试了非常多好玩的事情,比如:
“动手做”系列,我们做科学实验,简易的动力小车、小船,做木工,做美食,或是乐高机器人,等等;
探索社区系列,我们带孩子探索社区里的多元文化,例如不同地域的人的家乡美食,也探索社区里的自然资源,去附近的公园里做定向越野,也探索社区里的垃圾,或投放在不同地方的垃圾,到社区里废品站、再生资源加工厂,等等,最后一起把不同类别的废品,做成作品;
我们也带着孩子们去街上卖自己做的青团、粽子,或者去街上、广场、公园开音乐会。
我们把一直只是做观众的爸爸妈妈变成真正的参与者,和孩子们一起 pk 踩高跷、打陀螺、跳绳或是玩电子游戏,家长们玩得比孩子还嗨。我们曾经还组织了一群孩子和家长,到广州参加徒步公益活动。
▲2015年11月,组织科蚪空间孩子和家长参加徒步公益活动。
孩子们的确一到放学、放假,就有了一个去处。在读绘本《我想要爱》的时候,读到小熊“心里空空的,仿佛破了一个大洞”,一些孩子说,曾经,没有科蚪的时候,他们放了学,爸爸妈妈还在上班,自己一个人呆在家里的时候,心里就像破了一个洞。我们的确高质量地陪伴过我们计划服务的范围里 1/3 的孩子。现在,还会有家长对我说,感谢科蚪,那时曾经为孩子培养了好的阅读习惯,帮助孩子打下了好的能力基础。
我们也成功收了费,但,自负盈亏的目标失败了。
▲2016 年,科蚪空间孩子们探索社区小公园-倾听树的心跳。
我想我那时还没有在社区工作的恒心,也没有真正理解运营。所以,2017 年,我们关闭了这个空间。
这是我创业以后得到的第一个启发或教训:光能把一件事做得有意思,不代表什么。恒心更重要。创业者还需要理解,要解的这道题,是不是真的自己要持续求解的,要充分理解自己的底层动力和可能的阻力,知道自己是不是会长期投入这件事情。当然,找到自己的“命题”,探索期可能也是必不可少的。“科蚪空间”的探索,到这里,暂时结束了。
再出发
我回了北京。经历了一年的探索,2017 年末,我们开始筹备创办“实务学堂”。
这一年里,我尝试过把“科蚪空间”的一些课程做深度开发,做“规模化课程推广”。但我很快发现这完全不是我的兴趣所在。因为我在给孩子带去科技课程的同时,看到他们基础的小学语文都没学好。我上完 8 次课,就走了,似乎什么也不曾改变。
我就去了一所打工子弟学校,做初三班主任。我发现这些孩子基础能力非常薄弱,身心素质均堪忧,前途渺茫。所以,我想,可能接着初中,往下,为农民工子女探索一条职业发展路径,在现有的教育体系之外,开辟一种新的教育可能性,是重要的。
某种程度上小学毕业创业项目,做实务学堂也是一个冲动的决定。没有什么天时、地利、人和。正好北京大兴火灾,流动人口的处境都不太好了,这时候做一个面向打工者的学堂,会面临什么局势?也没有合适的场地,租了一个别墅,特别贵,场租占了一年运营成本的一半。也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全职团队,甚至,并没有多少学生,第一次筹建理事会,不少反对的声音。
我也对自己说,如果只是要做一些有价值的事情,就回媒体,也没什么丢人。但我觉得自己为农民工子女找到一个切中根本问题的解决办法,一个“学堂”,可以用三年时间,用一个新的系统,把那些已经被现有教育系统宣布淘汰的孩子,培养出来。
孔子说,“三十而立”。我当时也开始非常认真地思考了一个问题:当我老去,或者离开这个世界时,我希望自己给这个世界留下什么?
我希望我还是要做一件与“农民工子女”或“乡村孩子”有关的事。我自己生活在这个社区,我对这里的人有强烈的同理。我看到这里最深处的希望,也了解真实的问题在哪。
我知道没那么容易。但“难不难”不是我要考虑的,我只考虑它“对不对”,是不是真的能解决真实的需求。反正我准备花十年、二十年来做一件对的事情。我不需要快速的成功,更不需要证明我自己。对的事情,总是会有人来做的。成功不必在当下,也不必在我。
实务学堂初创三年,其实是一个很混沌的状态 — 不知道这是不是就是传说中的“青色组织”的生长。我自己一个人“分饰多角”,又当老师,又做管理,又负责运营。原因主要是没钱,没团队。
▲2018 年春季开学典礼合影。
先说说当老师的这三年多。
初为人师
当老师很需要稳定的理念、成熟的心智和丰富的经验。我在创办实务学堂之前,只在媒体带过实习生,在科蚪带过小朋友,在一个打工子弟学校当过半年班主任,我没有做过职业教育,没有真正去做这个年龄段孩子的老师。
我唯一的自信是,我曾经是一个“学渣”。我明白他/她们缺的东西,也相信“学渣”可以“逆袭”。就像我相信草根的生命力一样,我天然地相信这些孩子可以有美好的前程。我也还清晰地记得,自己是如何从零基础学习一些东西的。
另外,做记者这些年,我去过这个国家大多数的省份,走过许多的城市和乡村,领略过不同地域的自然风貌,接触过不同遭遇与面相的人民,见识过这个国家最出色的学者讲经济、法律制度,刑辩大律师的精彩抗辩,见到过一些闻所未闻的事情……这些见识、常识,连同大学教育一起,帮助我完成了自己的通识教育。在搭建课程体系时,我对课程和老师,有一些大致的判断。
最重要的是,我有长期目标,且有足够的耐心。我知道我不会放弃,努力陪伴和支持这些孩子。
我给自己定了一些底线原则,例如开放小学毕业创业项目,不伤害,有所为而且特别要有所不为。通俗一点来讲,对教育和孩子,要有敬畏,不懂的时候,不乱管。
做记者的时候,我知道自己的文字会带来影响,所以我总是很克制。当老师的时候,我也不能忽视自己的一言一行,可能带给其他老师和学生的影响。所以,我知道,哪怕我什么也不能教给这些孩子,至少,我不能去伤害他/她。
这个学堂,经历过很多变化(乃至搬迁),课程体系也不断迭代,但有一个东西,是特别难得稳定、一直没变的,那就是育人理念和基础规则。
育人理念三个词:诚实、勇敢、爱。禁止性的规则有八条,例如禁伤害、禁烟酒、禁教学时间玩游戏刷视频、禁夜不归宿,等。提倡性的原则有六条,例如保护自己的权益(感觉受到伤害可以表达不满、及时求助),等。
只立底线原则,不立学生记不住也执行不了的规则,这是为了底线或管理的边界,尽可能清楚、被尊重。实务学堂创办三年多,没有发生过打架斗殴事件,甚至在公共场合说脏话的事情都非常鲜有。
对老师,一直以来,因为绝大部分授课教师是志愿者,是一群本身自驱力和使命感都很强的人,因为很多来自实务一线,专业能力普遍也很高。我在做教师管理时,也要求自己尽可能不要做“绊脚石”,给老师比较大的自主空间,尽可能尊重、支持,而不是随便指手画脚。当然,后来有新老师加入,我们的课程体系已经相对清楚,所以也会直接执行既有的教学计划。
实务学堂创办三年多,申请成为志愿者的老师,平均每年会有 100 多人。我们每学期都会有二三十个持续教一学期的志愿者,而且,有十多个老师,能持续参与教学两三年之久。这可能也是奇迹。
▲2019秋季生日会。
矛盾
作为老师,可能有两年的时间,我都处在一个矛盾之中:对学生,期待多高、管到多少,才是合适的度?
一开始,我很担心,管多了,这些孩子吃不住,因为很多学生就是以前传统学校的“学困生”。我本身是一个自由惯了的人,并不喜欢“好为人师”。谁也不愿意被学生害怕、抗拒。
但我就想开了,不要低估他/她们的学习意愿和抗压力,也不要高估他/她们的自律。重要的是,老师和学生,是否有真正的共识。
我后来意识到,“学困生”并不是我们真实的“目标用户”。一个表现是,第一年招收的学生,留存率特别低,很多读了一学期就走了,2018 年入学的学生,完成了完整学习,或今年依然在学堂的,只有 4 个。从事后看,第一年的工作,很像是在错误起点的“测试”。
后来,我们在招生时增加了面试,虽然依然不以过往学业成绩为录取依据,但增加了对身心健康、求学意愿的考查。这之后,学生人数反而多了(也因为过去一年多的持续努力),2019 年秋季到 2020 年春季,我们有 28 个学生,是此前一年的两倍多。学生的留存率也反而高起来了,虽然经历过多次搬家,疫情中也有学生流失,但大部分学生一直留在学堂。
▲2019年秋季学期实务学堂开学典礼。摄影:曹雕。
学生要为更好的工作、生活做准备,老师尽力提供支持,在这个基础上,教学和管理逻辑终于通了。
创建一个宽容、有爱的环境,让学生感觉到安全、自在,而不是恐惧,这是我们一直在做的,也是被人们所熟知的部分,也很符合人们对“创新教育”的想象。但其实,我们并不是没有要求。
最近凤凰网“在人间”上线的纪录片《独木桥之外》,跟踪了我们半年,拍到了一个细节:2019,我们承接了一个知名车企的项目,培训我们的学生到中小学讲交通安全知识。两个学生想做讲师,但晚上试讲没通过。如果想登上讲台,必须试讲通过。
他们重新“背稿”,一直准备到凌晨一点多,并且让生活老师早上五六点就叫他们起床(因为晚上手机被收了,他们没有闹钟),“如果我们没醒,多推我几下,好么?”
早上七点半,我还没到学堂,他们找了“讲师培训”负责人(也是一个学生),给我发了视频,做了第二次试讲,最后顺利通过。
第二年,因为我们此前一年的出色工作,我们又拿到了这个企业的委托。我们对讲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学生们依然需要一轮轮地试讲,争取“offer”。但结果是很美好的 — 他(她)们可以得到项目津贴,并且能去从未去过的云南增长见识。
我们承接项目,核心目的是给学生学习成长的机会,但尊重工作、尊重交付方的要求、靠自己的努力获取自己的收入,正是首先需要学习的职业能力和品质。
学堂内部的勤工俭学岗位也是如此,我们要给学生机会,但能力与意愿都欠缺的话,那就很遗憾不能被录用了。
这些孩子,离开实务学堂,就要在社会上独立生存。我们应该一起学习职场与社会的基本规则。
▲2019 年,实务学堂学生参访世界 500 强企业
我会努力给学生们争取实践和实习机会,让学生们尽快去职场学习技能和规则。即便有些老师觉得学生还没准备得足够好,但,没有人可以为他(她)们做永远的保护者。
但,我们可以一直做坚定的支持者。最重要的支持是两方面:一方面是给能力成长的“脚手架”,知道哪些能力需要,就要有哪些课程支持;另一方面是陪伴与情感支持,成长中遇到挫折,老师随时可以做“树洞”。
小成就
到今年,我们已经有了两个毕业生。一个在科技公司做程序员,一个留在学堂实习半年多以后,即将去做运营。今年夏天,我们还会有第三个毕业生,其余学生基本会在明年春夏两季毕业。做程序员的毕业生,收入已经超过了学堂的所有全职老师,而他老家的同学还在读大一,或是正在参加第二次高考。最让我们骄傲的,不是他的收入,而是正如他的上司给他的评价,“学习能力强,做事认真负责且走心”,并且,利他精神深入骨髓 — 他依然把学堂当作自己的家,每周回来,给我们提供支持。
除了把项目外包、实习机会给我们的企业、机构,我们也开始积累了一些有联合培养或招聘意向的合作企业、机构。
2019 年春季入学的 D 同学,最近计划报名一个论坛的演讲。他跟我说,他计划讲讲自己的学习经历,从“不想学”到“想学”的转折。
这又激发了我的好奇心:“转折是怎么发生的?”
“一个好的氛围。”他回答,老师们并非不可质疑,也不是让自己不敢表达、提问的,“我会去想,那为什么是这样?这样做对吗?思考的过程,找答案的过程,其实学习就发生了。”
他来到学堂的时候,说自己彷佛抓住了一个悬崖边的木桩,希望抓住机会,爬上去。再有半年,他就要毕业了。现在,他在一家教育公益机构实习。
大小伙子了!我心里想。
“加油,特别期待你的演讲。快毕业了,真是让人充满希望。”我说。
▲学生们自己组织的游学,参观大学。
草创
总是打满鸡血、努力求生,总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这可能是过去几年,尤其是做实务学堂后三年半,我作为创业者、校长,最真实的心态。
战战兢兢是因为,这是一个“全日制”的教育项目,每个学期结束,一切平安,我就感恩戴德:感谢上天,感谢所有老师、学生和家长。有时候我想,要是不做实务学堂校长了,我真的要躲在哪个地方“自闭”一段时间。
从创办实务学堂第一天起,我给自己定的第一目标是:让实务学堂活下来,尽可能活得久一点,先活十年,再活二十年……“百年树人”,人的成长周期是很长的,所以,学堂也必须活得久一点,才能有稳定的教育哲学,才能更深厚的功力,成就学生。
其实,“活下来”也并不是容易的事情。但:
“
底层的人,或者说“草根”……非常善于用极少的资源,在极难的条件下,寻找到生机,非常善于自得其乐,总是相信,日子总会越来越好的。
在农村生活过的这些人……对匮乏非常熟悉。我的父母亲在外面打工二十多年……做过各种各样的事情,收废品、进工厂、缝补衣服,开出租屋、台球桌,也开过早餐店、餐馆,住过桥洞、工棚、自己搭的简易房,住过各种各样不透光的房子,但是,他们好像也没有觉得日子不能过下去。
”
所以,我也这样期待自己:把日子好好过下去,好好经营下去。
如果我相信这个社区需要好的教育,我就相信,这个学堂就可以活下去。因为,这个社区会有力量让它活下去。
过去的几年,我们搬了许多次家,多到我自己有时候也记不得到底是五次还是六次了,相当于前三年,平均每学期搬一次。2019 年春季,为了省场租,我们搬了第一次,搬到西北六环外,这里离市区很远,没什么人烟,但在这种地方,场地方自己都经营不下去了,我们也就只能继续搬。但总是柳暗花明,学堂理事大车老师这时接纳了我们,我们用不贵的租金,获得了新场地。这里又搬了一次。
紧接着就是疫情,我们“搬”到网上,上了一学期课。最后,我们整体搬到了广州 — 先在帽峰山短暂停留,然后搬到小洲村落地。
三年下来,尽管经历了许多波折,以及我们所未料想过的疫情,我们挺了过来,且尚有一点应对风险的能力。当然,我也是心有愧疚的,团队、家人,都受了累。
▲搬到广州后,我们不止一次见到彩虹,风雨后,会有彩虹么
有时候,我想,为什么在反复搬迁中,学生都没有离开学堂,甚至在搬到广州时,真的没有一个学生离开?
我觉得,可能正是实务学堂做的,是他(她)们真正期待的教育,甚至在搬迁、遇到困难的处境时,依然在实践这样的教育。正如我曾经和学生们说的:
如果说,我希望学堂的同学们,能从过去我们的艰苦生活中得到什么益处,那就是,我希望同学们在这里不只是学习 to learn(去学习),更能学习到 to earn(去生存),希望你们都保持生命力,去争取、去谋求、去创造自己更好的生活。我相信有这样的生命力,在哪里都能活下去。
学生曾经可能开玩笑也可能当真地说:“学堂搬家的经历,值一千万。”
他们承担了学堂越来越多的运营工作,比如传播、教学、卫生管理,等等。我在这些经历中学习、成长,他们也是如此。
我们搬到广州,是看到了一个未来:草创阶段,快要结束了。我们应该考虑长远的未来。
在疫情尚未结束、社会充满挑战的时代,说“长远”,有时候是奢侈的。但我还是想去搏取一个尽可能远的“长远”。所以,当我们找到场地时,向房东提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租约可以签十年以上吗?”得到肯定的回答,我们期待在这里扎根下来。
过去三年,我有如草莽,一个人扮演了多个角色,靠着热情、直觉,还有他人的帮助,把实务学堂运营了下来。但这不是未来我们需要的。我自己的角色,要逐渐厘清。我们要有团队,有机构治理,有机制建设。这些都是我们未来面临的新问题。
▲我的写作课。
如果,回到六年前,我会做出同样的选择吗?我不知道。
但是,站在今天,我觉得,至少,我当时做出了一个对的选择。
– END –